

薅 苞 谷
王义
我当知青时,把春夏之交在山坡大面积种苞谷的庄稼地除草叫做“薅包谷“,也就是所谓的“薅草”。
但是,在我插队落户的黄平县上塘公社黄泥坡生产队的“薅包谷”远不止是“薅草”,其内涵丰富得多:除去要疏松土壤、要疏松土壤、除草因素,使庄稼更利于吸收营养,要重新给庄稼扶上泥土,以使庄稼保肥抗倒伏。而这些都是庄稼在秋收时好收成的基本保证,但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民俗文化现象。
“薅包谷”有一道、二道、三道之分……
时间一般在农历四月至六月中旬。端午节栽完稻秧后,就开始薅苞谷了。
此时薅苞谷除了除草,还有为了扶泥和除去多余的苞谷苗,俗称“疏苗,让经过选择剩下的苞谷在暴风雨盛行的季节增强抗倒伏的能力,确保收成。
“薅苞谷”是要选好天气的。什么样的天气最好?晴天,太阳越大越好越适合。“农业六十条上的保墒增肥力”、“锄头底下有把火、锄头底下有股水。”大概就是直指此。特别是指有效除草的前提。
黄泥坡生产队的虽地势较高,多数地质构造是喀斯特地形,却因其地处亚热带,并不缺乏小平原、麻窝土等大块或较大块的地,更不缺乏充足的阳光、湿度、温度和肥沃的土壤,故而不但庄稼长得蓬蓬勃勃,而且各种杂草在春天温暖的春阳里也是呼啦啦一天一个样地疯长的。如果不选一个太阳越大越好的天气,“薅”也是白“薅”——比如刚薅好就逢着一场雨,那些已经铲倒的杂草的依然会重长出新的根,没有薅干净的残草顿时就在雨后的地里高调地再次站立起来。
在气象预报并不发达的年代,选好天气其实并不容易。
当地看天气的民谚依稀还记得:“云跑旧州城,不晴都要晴。”、“云朝东、一场空,云朝南、雨成团,云朝西、雨稀稀,云朝北、晒荞麦。”也就是说,看到云往旧州城方向运动,就要天晴了,就可以“薅苞谷”了——黄泥坡生产队在旧州城的西南部,当东南风盛行的时候,就推动着大气往旧州城所在的西北方向运动,故而看到云是“跑旧州城”的。这实际上是“云朝北,晒荞麦”的民谚在我们独孔垄的变种。
节令不饶人,因为好天气是不等人的。按照如今气象台天气预报的说法,我们所处的海拔约1500公尺的白岩上空经常盘踞着一大块云,只要一安营扎寨,就不大肯轻易挪窝——别的地方早天晴了,我们这里还是一片烟雨空濛。所以一俟有晴天动向,我们就要在乡亲的催促下及时行动。
通常,我们由寨子上有农事经验的老农要在头天晚上看好天象,作好预测。天一黑就睡下,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左右就起床,在“早上工啊早上工,三个早上顶一工。”的民谣中,扛上锄头,背上马草箩,担上高挑,带上早早就热好的饭就出发了。
此时正是晨光熹微,山路上视线还很模糊,可是到得地里却正是最佳劳作时候——我们要趁着热辣辣的阳光大肆登场之前,薅出一大片包谷地让阳光晒草。
下了地,队长做了简单的分配之后我们就开始紧张的劳作了。
大致程序是:雪亮的锄头不深不浅地翻起自春耕以来一个多月平静的土壤,把那些白花花的蒿草、鹅耳草、肥猪苗等杂草的根翻起来,用手把它们从土壤里拔出来,嫩嫩的苗用草箩背回去喂牲口,那些白花花的草根抖干净了泥,摆在新鲜的泥土上等着太阳出来晒;然后用锄头刀刃处的尖角对准包谷窝处的植株间的泥土,把土壤薅松,以便吸收施用的粪肥或复合肥;再给植株扶上泥土。
给苞谷培土的环节要看苞谷种,以前我们黄泥坡的苞谷根系不很发达,吸收地里营养的功能似乎要弱一些,抗倒伏的功能也比较差,所以薅铲时要多扶些土。但这种叫糯苞谷以后磨成米做成的饭好吃,所以即使多费些劲我们也愿意种。
薅一道苞谷不只是使劲用锄头挖土,使劲除草,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定苗,亦即定每一窝的植株数量。因为是第一次下地薅苞谷,我们得按当地的惯例,一窝苞谷的植株一般就是两棵,而播种的时候都要多播几粒种子以确保每窝植株的数量,有些年份,植株都生得齐,数量就超标了,这时候就要把一些已经长得不大不小的苞谷苗拔掉,以确保营养之需——这也是植物界的“计划生育”。所以这一步很是需要下一番狠心的——已经长成的嫩嫩的绿绿的苞谷苗被人无情地拔起来,带回家去当作了家中牲口的美味,真是可惜啊!可是不坚决拔掉,一定会影响秋后的收成的。那时我通常都不大能狠心拔掉多余的苗,但遇着老农参加劳动的时候,都会坚决拔掉。
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就是当时的写照。
不过,“懒人也有懒办法”。我边薅边给旁边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的“小嘎兜”(少年)们讲《西游记》,这样一来,的确减轻了我的劳力。有时我也象说书人一样,到故事关键时,卖一下关子,于是乎,求知欲极强的“小嘎兜”们,就会帮我多薅一些,好让我多摆一些“孙悟空大闹盘絲洞”之类的故事。
我们多是苞谷、大豆、红豆等多品种间作:虹豆跟包谷一起呆在窝里;肥地里一行包谷一行大豆间作,痩地里一行苞谷一行红豆——红豆这东西最贱,不管怎样痩的地,只要播种后秋收都能有好收成;至于高粱啦,葵花啦什么的,人们是舍不得专用地来种它们的,多是在种好包谷后撒在地里,随便它们能不能生出苗来,任其发展。这样的间作方式也给薅草带来很大难度:若是只一心除草,就会无意伤着甚至挖掉这些作物的苗——既然苗已长出,就要好好保护,所以只好把薅铲的速度慢下来,同时做到除草保苗扶泥土多重兼顾。
但是“薅苞谷”是有季节限制的,太慢了就会延误农时,故而“薅苞谷”的环节不但工程量较大,而且时间紧,通常都要做到早出晚归。为了把草薅出来给太阳晒,中午常要顶住烈日干活。这时,人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敞开了大门,一任汗水汩汩冒出来,顺着脸颊、脖子,汇聚到胸脯,背沟,直至裤脚处流出,岂是古诗里一句“汗滴禾下土”或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所能描述?此时人浑身发麻,眼睛发花,几乎失去了意念和知觉,却仍要坚持着。
特别是薅三道包谷的但此时正是盛夏季节,苞谷苗拔节也高过了人头,在苞谷林里劳作,一面要接受火辣辣的阳光的考验,一面苞谷叶子要在人的脸上、脖子上、胳膊上割出一些口子。这样一来,汗水流出来后就径直渗进这些鲜红的伤口,给人肌肤上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。
天太热,但又不能光肩干活,只好穿着长袖衫下地。中途小憩时,就会有人提议唱歌解乏,他们唱的山歌我们根本不会也不懂,我们知青只会唱“毛主席语录歌”和“外国民歌”,何况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唱?
当地唱薅草歌的时间有一定的习惯,清早是不唱的,因为早起刚开始做活, 人很精神, 不需要提神, 等到太阳高照人被晒得很昏沉, 这时就要唱了, 大家边唱边薅, 精神来了, 磕睡、疲惫就自然逃走了, 干活就更有劲。记得那些经常串“马郎坡”的男青年就会唱道:
“红笼帐子绿帐檐,苏州麻布剪刀圆,
妹是苏州红缎子,哥是麻布配不全.”
另一边唱薅草歌的
“红笼帐子绿帐沿,绸缎被容花枕边,
绸缎被窝妹不爱,情愿跟哥盖草被。”
男青年唱道:
“红笼帐子绿帐沿,二龙抢宝在中间,
哥是龙来妹是宝,情投意合换新天。”
小媳妇就答道:
“红笼帐子绿边边,二龙抢宝在中间,
龙凤呈祥花结彩,好花开在情义间。”
……
这些富有民间习俗的文化现象,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,并没有什么感受,只知道正好趁机多“撑一下锄头把”。
这种高吭抒情的曲调在广袤的田野上, 此起彼落确实非常动人, 如果不是老人们怕担误活路进行干预的话,这样一直要唱到太阳落山天黑收工时才停止。我想,这些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文化大革命“破四旧”怎么没有把它彻底破掉呢?或许是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原因吧。更也许是老“摇马郎”对年轻未来的“摇马郎”一种“生存繁衍”的展示和经验传授吧。
收工回到家后,早已饿得前胸巴后背我,匆忙中胡乱填饱肚子,连平时喜欢拉奏的“可爱的家”、“南京知青之歌”这一些我喜欢的歌曲都没有一点兴趣,洗完脸、脚后,倒头一觉睡到天亮。
这种生活一直到要三道苞谷薅完才暂时告一段落。
虽然这段农耕生活的艰难和痛苦处,却也是我人生的一种有效磨砺。经历过这种劳动的我,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几乎都不怕吃苦,不但多了一份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,更少了一分对困难和挫折的畏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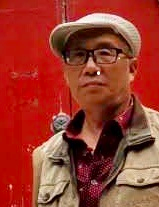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王义(艺)原贵州省话剧团舞台美术主任技师(副研究员),现为《中国绘画年鉴》画院贵州分院院长、民进贵州省文化委员会副主任、民进贵州开明画院理事、贵州省师范学院文化与教育合作研究院研究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音乐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舞台美术学会常务理事、贵州省影视文化艺术中心主任编导。曾参与电视专题片《天地绝唱——走向世界的贵州原生态音乐》(该片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出版物提名奖)、《您了解艾滋病吗?》、《古、奇、险、幽话福泉》、《艺术殿堂的明珠——音乐》等,后参与《贵州民间美术传承保护》(该课题获贵州省第9次哲学社会科学3等奖)、《中国西部阳戏文化带相关问题研究》国家级社科类课题(该课题获贵州省第11次哲学社会科学3等奖)和《贵州省龙里巫山岩画研究》、《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研究》、《贵州民族民间戏剧研究》等省级社科类课题、现已出版专著《坑坑洼洼》、《艺文选辑》电影文学剧本《倪儿关》和即将出版的《舞台美术造型概论》,合著《贵州傩戏文化研究》(该书获“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著作”、“贵州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专著类二等奖”)、《贵州民歌艺术论》。主要研究范围:社会学、人类文化学、美学。曾在国内外有关刊物发表多篇学术性文章。
 贵公网安备52019002007322号
贵公网安备5201900200732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