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龚滩人物:往事依稀浑似梦
易 光
往事依稀浑似梦
都随风雨到心头
——《词林纪事》(上卷)
在《词林纪事》(上卷)第二六八页的天头,有人用蓝色墨水写下两行诗:“往事依稀浑似梦,都随风雨到心头。”字体端庄隽秀,当是老友杜君所手书。《词林纪事》是我们所珍爱的一部书,不会流入他人之手。不知道杜君何时所写。可以推断的是,1968年底我从县城回家种地之后,它就再也没有回到我的身边。杜君无论写于上世纪70年代还是80年代,有这种心境,都是可以理解的。
我何尝没有“往事依稀浑似梦”的感觉?
我都已经把《词林纪事》遗忘了,却不料它居然再次回到身边。
2010年11月1日,我回到老家龚滩古镇看望姐姐和姐夫。从车站下行,路过仿造织女楼,不顾旅途劳顿,立即去拜望杜君。从邻人处打听到他的家门口,拍动板门,应声而开,他夫人却已认不出我来。杜君闻声出庭,才把我迎进院内。
第二天下午,我正式去探望他。我们手握一杯清茶,回忆当年友谊。说得更多的,是当年的抵足而眠,彻夜长谈,吟诵诗词。说到词,他说,我要把一件东西还给你。他把“还”字说得很慢很重,显然是准备了很久。是什么呢?一本书,一本宋词。我立即叫出来:“《词林纪事》!”
杜君颔首而笑:“对!”
《词林纪事》是文革中我同几位同学晚上窃入某图书馆偷来的书。它应该是上下册。分赃时,以江湖义气,我独得这一套书是不行的,只得忍痛割爱,心怀耿耿,以至于今。那位执意分去下册的邱姓同学,地处宜居乡,却不当道,自打分手,再未谋面。做鲁迅之叹,“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”?今天要得到1957年8月古典文学出版社一版一印全套,已不是难事,但在我,却是一段难忘的历史记忆。
杜君捧出书来,那番奇形怪状,让我好笑又吃惊。外包装是深紫色毛选第一卷布面精装封面,打开来,是灰黑的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内页。这是典型的文革黑色幽默。毛的神圣的大旗,又一次做了下愚们的虎皮,将封建文人张宗橚包裹起来,深藏起来。毛渐行渐远,张宗橚却悄不声向我走来。这真是时代的悲喜剧!
我们就吟哦起那些曾经熟知的词章。李煜。范仲淹。柳永。苏轼。秦观。辛弃疾。以那时的心境,我们更喜欢婉约派的缠绵悱恻,凄清悲凉。比如李煜,柳永,秦观。比如李煜的《虞美人》: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?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! 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。”不知谁为这首词谱了曲,杜君会唱,唱来苍凉激越,百转千回。我也很快学会,至今能一拍不拉地唱出来。
杜君那因为心脏病而衍出的青灰,竟有了几许红润,那部花白胡子,得意忘形到颤动起来!
我欣然接受了杜君的赠予。因为这书当年本不属于我,而是一位爱书的读书人“窃”取了它。后来也不属于我个人。我们曾经偷偷做了个夹壁,把我的一些书和他所有的书藏起来。这是真正的藏,不敢为外人道。为了那时我的和他的特殊身份。这个小小的私人图书馆,后来毁于古镇的一场大火。最为繁华的一段商业街,在大火中化为灰烬,连同我们的那些视做身家性命的书。《词林纪事》为什么会得以幸存?这是我们共同的痛,我不敢追问。
临出门时,情节却出现小小的转折。
杜君说:“这书你今天还不能拿走。”我心里小小一惊,莫不他变卦了?他说:“你不是还要下乡吗?你回头再来拿。我要把一些词抄下来。”我说好的好的,但你可要“君子一言”哟!我这是玩笑,但愿他不要看到我猴急急的穷样。
出门时心里想:他会抄些什么词下来?除了怀旧,他还会从文学的角度去对一些词激情万状么?
去乡下时,居然又撞上一件难得的文事。1959年时,我从寨子里一位兄长处借得一本《说岳全传》,读得是大快朵颐。这是我所读第三部长篇小说,又是第一部古典小说,意义非常。在寨子里一幢老宅前撞见这位兄长,说怕还能够找到。果然就被他从什么地方找了出来,只是更加惨不忍睹。承蒙他慷慨赠我。要在城里旧书店,这叠破纸屁钱不值,我却视为珍宝,千恩万谢,收拾下山。
这时接到杜君电话,约回古镇那天,一定喝一杯。我说好的好的,只是喝的吃的尽可能从简。
下午6时,如约前往杜君家。此时古镇已是黄昏。初冬时节,古镇游客稀少,大街很显寥落。
杜君早已等候在楼下的门口。他的新居,临街本有大门,他却只从右旁一米宽的石梯上下,这石梯直通他家后门,有一块七八平米大小的空地,背靠一面山崖,仰起头来,只见蓝天白云。杜君因之戏称蛙园。井蛙而自有天地,只要不妄自称大,亦是一种境界。
酒是自泡药酒,浓酽的橙红,淡淡的酒香和药香,未曾举杯,先自醉了。菜却并未从简,杜君的夫人很会做菜,摆满了一桌。卤猪蹄膀,横切成圆形的片,晶亮的肉皮,环护着瘦肉,如镶金嵌银。一盘泡菜磨芋,本地土法制做的老磨芋,青灰颜色,特别地香,防癌治癌的功效就会更加地好。木耳肉片,有馆子的水平,不像乡下的炒肉,丝不像丝,片不像片,不成形状。一碟碧绿的胡豆,入口即酥,问起来,说是春末新胡豆上市时,买来冻在冰箱里,绝对保鲜保嫩,正好下酒。
话题就从胡豆开始。说2007年11月去绍兴,特意去咸亨酒店喝黄酒,就茴香豆。孔乙己的故事,虽然亦真亦幻,我们读书人身上,不都或多或少有孔乙己的影子么?冒酸,很把自己当回事,却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风浪中一叶不由自主的小舟。杜君也喜欢鲁迅,文革中更可以光明正大地读,就成了案头必备书。读鲁迅杂文,也会在暗夜里笑,笑什么,却苦涩而茫然。
这次谈话,很小心翼翼,怕累着他,更怕他激动。他却说:“问题不大,没事!”酒更不敢劝他多喝。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只小杯子,倒小半杯酒,小口小口抿,也无非陪我,意思一下。但喝到一半,他突然起身,钻进另一间房里,搂一卷纸出来,转着圈找地方,把我看得莫名其妙。
待他把那卷纸打开,往木板墙上按压图钉时,我才看清,这是一幅书法横轴,行书抄录的,是他自己的作品《蛙园记》。我赶紧过去帮忙,摆放周正了,他端详了一刻,脸上渐次涌出自得的神情。我读出来:我还不老,仍有激情和想象力!
现借块地方,把杜君大作先予发表:
蛙园记
己酉之秋,时值文革,移民郑氏失火,累及古镇,二村数百幢楼房付之一炬,余家亦在劫矣。既赁一村百年老宅二间,一楼一底,矮而陋,伸手可及楼顶,容膝而已。后公房拍卖,而无力移迁,遂置之。然数百元价,已倾其所积矣。
前临古街,楼后一空地,仅十余平米。余围以砖,使不外通,内砌小鱼池,置数盆花草。侧系柴房并书斋,缘四面皆高,如处井底,犹余之其人,遂戏名曰蛙园。
余一生碌碌,时乖运蹇,无情岁月,吞尽华年梦想,不堪回首。有幸桑榆迎来盛世承平,颇慰老怀。吾爱蛙园简朴幽静,无事闭目神思,有时浅唱低吟,兴来挥毫泼墨,最喜描影雕根。春有玫瑰灼目,夏有茉莉飘香,秋有黄花满径,冬有红梅盈枝。犹喜初夏,小鸟啁啾,喙食紫红桑椹,纷纷坠落。满园流丹,喜生命之斑斓。秋风起处,房后古树声然。黄桷树叶,漫天飘零,颇感肃煞。叹人生之无常,然绝无噪音之乱耳,更无暴客之敲门,乐在其中。虽无退休金以资养老,喜有儿女孝足以颐年。尝谓人曰:“布衣素食,可傲王侯矣!”竟日俯仰偃卧,笑傲其间,荣辱俱忘,不知老之将至,复何图哉!
壬午年三月,随次子鹍去晋,初出蛙园,外面世界真精彩。偶念及龚滩古镇故居,感慨系之。遂写以上文字,就名《蛙园记》吧。
蛙园叟 壬午年四月廿二日撰于晋
甲申年重阳书于蛙园
读罢杜君大作《蛙园记》,我不由也是“感慨系之”!
己酉(1969年)秋,我从县城中学回乡下种田,已是一年有奇。从初始的“满面蒙羞”(读了十几年的书,仍是回乡当泥腿子,还让父亲吃了大苦头,令亲者痛仇者快),到渐渐麻木,埋头学做农事,成为一个地道农夫。我以农夫身份,前去龚滩古镇办事。龚滩既是区政府所在地,也是这片地域繁华的商埠。那时似乎还在毫无希望地爱恋着一位女孩子,每过一段时日,就会踅去三十里外的古镇转转。这一转就转到火灾现场。这已经是大火之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,数百米长街,一片焦黑中尚有余烟袅袅,其状惨不忍睹。我踅到杜君老屋,面对那一片余烬,哀悼我们的那些图书,痛彻心扉。揣度起来,烟荒火乱中,除了生活必备,杜君也来不及抢救出些什么,不敢抢救些什么。那些不能见天日的封资修。那一刻,我只能默默地为封资修们送行:Adi,我的唐吉诃德们!Adi,我的《词林纪事》!
《词林纪事》怎么会保存下来,我不知道。不要说那些书,就连杜君,也似乎已从地球上消失,无处寻觅。直到如《蛙园记》所述,后来他租赁到一村(龚滩古镇划分为三个行政村,一村居于上游,比较偏僻)那座矮而陋的百年老宅,我们才得以重新相见。我们都避而不谈那场大火。杜君简陋的书架上,除了毛选,就只有零星几册市面能够买到的鲁迅著作单行本,《彷徨》《呐喊》《朝花夕拾》之类。元气大伤,以至于今,要东山再起,很难很难。或许那时《词林纪事》正相伴左右,成为杜君文学阅读上唯一的精神支撑。
这时杜君已不再需要这根坚韧有力的拐杖?他是更坚强了,还是已然向命运屈服?
我知道他正等着我对《蛙园记》做出评价。
我说作品非常不错。
我说书法也不错,功底深厚。我忘了说,杜君的书法,还真有王羲之的风格。
这样就更使我的评论单调空泛,听起来绝对搪塞之辞。
我们又吃菜喝酒。这让我有了缓冲,来调节一下我的思路。
我说这次来老家,看过朋友做的一些赋,虽然不便批评,但也绝不违心地送上一摞摞好话。我说这些所谓赋,虽然辞章铺张扬厉,有的甚至中规中矩,但缺乏灵魂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之所以流传千古,不仅辞章华美,更有魂魄做砥柱中流。我不敢卖弄,比如“时运不济,命运多舛。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。屈贾谊于长沙,非无圣主;窜梁鸿于海曲,岂乏明时。所赖君子安贫,达人知命。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?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以犹欢。北海虽赊,扶摇可接;东隅已逝,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,空怀报国之心;阮藉猖狂,岂效穷途之哭!”比如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;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”,都为杜君所烂熟于心 。其实,《蛙园记》多可见出它们的影响。
我说《蛙园记》虽不敢上追王、范,却也有自己的名段佳句。比如“叹人生之无常,绝无噪音之乱耳,更无暴客之敲门,乐在其中”,如洪钟撞响,余音绕梁。结句“尝谓人曰:‘布衣素食,可傲王侯矣!’竟日俯仰偃卧,笑傲其间,荣辱俱忘,不知老之将至,复何图哉!”,其高洁的精神气象,振提全篇,响遏行云。通而观之,并无落荒颓唐之伤,既是生存哲学,亦是抗议和挑战,妙哉已也!
这一番说辞,有根有底,直说得杜君自己也热血沸腾,荡气回肠,脸放红光。
有此铺垫,我就好来说它的不足。
我说古文功底,我是远逊于杜君。
先说“盛世承平”。这最为打眼。我几乎声色俱厉,说“盛世”从来没有,以这架势下去,永远也不会有!以兄长之才学,本是栋梁之材,却被弃而不用。豺狼当道,虎豹横行,乱了数十年天下,从未治过。承平之说,从何说起?又说当下,古镇搬迁,兄长居处大有改善,却是以健康作为惨重代价,因拆迁重建劳累过度而发病,几至不起,谁的过错?
杜君微微颔首,心似有所动。
话题转到篇章结构上。我说兄如再做润色,可否考虑增加文学影响内容?兄几十年身处逆境,而不自暴自弃,得文学荫庇多矣。是文学使井蛙既能自度自省,又眼界开阔,想象激越。是文学使我辈与世间众多俗人厘清泾渭,而高昂起一颗尊贵的头颅,睥睨万物。没有文学,便没有我们的今天!
我自己倒先激动起来。
酒杯空了,饭菜凉了,人心暖了,我们应该告辞了。
没忘记虎口夺食,捧走《词林纪事》。
几天后,回到讨生活的城市。小心翼翼细检《词林纪事》,又生出千般感慨。
据研究者所言,《词林纪事》系词话集,为清代张宗橚辑。宗橚字泳川,号思岩,海盐(今属浙江省)人。生卒年不详。康熙乾隆间人。太学生,不求闻达。早年受业于许昂霄,许昂霄精于词学,张宗橚受其影响。著有《藕村词存》。此书是编者晚年所辑,三易其稿而后成。全书22卷,辑录唐词1卷,五代词1卷,宋词17卷,金词1卷,元词2卷,共收词人422家,大体依词人时代先后,排比分卷,条贯清晰。所录词人附有其生平事迹、轶闻,以及有关词人所作词的评论,所录词征引本事,间有考证,搜集资料比较丰富,引用书目达395种。书中又多引许昂霄对于词的见解,间附编者按语,亦多精确。所引书皆注明出处,但不尽依原文,多随意增删,致失其本来面目。所征引本事,有的不直录宋人载籍,而转引明、清人词书,故有差误。
《词林纪事》有乾隆刻本,道光刻本。古典文学出版社用前上海杂志公司纸型(1936)重印,并据涉园张氏刻本做了校订,195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,首印1.1万册,之后似未见重印。稍后又有中华书局版(1959)。手中的《词林纪事》,无封面封底,从出版说明残页看,当属古典文学版。
在《词林纪事》中,留有许多着重号,也有少量文字。这些着重号,有我加的,也有杜君加的,以我加的居多。研究这些符号,可以破译那时的我们,对《词林纪事》(特别是唐宋词)的情感态度和理解能力。
那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密码。
我首先用毛笔为《词林纪事》总目的上册部分,做了个页码。
正文部分,从李白起,我用红铅笔在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上加了三角符号。这两首作者存有争议的词,委实不错,我现在还能背诵。杜君还另外喜欢李白的《清平调》。其一云:“一枝红艳露凝香/云雨巫山枉断肠/借问汉宫谁得似/可怜飞燕倚新粧”。
杜君的审美品位,自然在我之上。还有不同的,我侧重在幽怨惆怅一类,他则兴趣广泛得多,包括儿女情长一类。
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,是我们都喜欢的。他喜欢画画,自然把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当画来读,我更多喜欢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那种情调。
但那时我不理解,他为什么还喜欢韩翃的《章台柳》:“章台柳/章台柳/昔日青青今在否/纵使长条似旧垂/也应攀折他人手”。这是韩写寄给柳氏的。张宗橚援引《太平广记》说:“韩君平有友人,每将妙伎柳氏至其居,窥韩所与往还皆名人,必不久贫贱,许配之。未几,韩从辟淄青,置柳都下。三岁,寄以词云云。柳畣以杨柳枝云云。后为番将沙叱利所劫,有虞候许俊诈取得之,诏归韩。”柳氏回寄的《杨柳枝》云:“杨柳枝,芳菲节,可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,纵使君来岂堪折。”一个古代文人的艳情故事,杜君竟为之所动,我至今不解其中隐秘。还有白居易的《花非花》:“花非花/雾非雾/夜半来/天明去/来如春梦不多时/去似朝云无觅处”,也有异曲同叹之隐。
到李璟李煜父子部分,我们批加的符号就多起来。
我喜欢李璟的“细雨梦回鸡塞远/小楼吹彻玉笙寒”。杜君则在“风里落花谁是主/思悠悠”一侧加了着重线。(均见《山花子》)其他《浪淘沙》,《虞美人》,更是我们常常吟咏的名篇。《虞美人》是我们的保留节目,两杯烧酒下肚,我们便击节而歌: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?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 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!”我们会把尾音拖得很长,全不管音乐的法度。李煜的亡国之音,在一个僻远的角落,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。
说到击节而歌,我还从杜君那里学到岳飞的《满江红》:“怒发冲冠,凭阑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 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?驾长车、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。”这时是豪放与悲壮一起涌流而出。为岳飞壮志难酬扼腕而叹,也叹我们自己的 “三十功名尘与土”。那时杜君早过而立之年, 却是功不成,名不就。我则更惨,连温饱也常付阙如。至于“朝天阙”,虽处江湖之远,何曾有资格仰视圣颜?要忧也是白忧。
宋祁的诗词,在宋人中并非名家,我却特别喜欢他的两首词。一首是《鹧鸪天》:“画毂彫鞍狭路逢。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 金作屋,玉为笼。车如流水马游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几万重。”那时我或许在恋爱,却是一桩无望的爱情。相距并非遥不可及,但那种失望,真在蓬山之外。杜君如能记起,我曾托他作伐,得到对方父母的回答是:“绝不可能!”其理由是:“没有这种规矩。”那一段时日,如处冰窖。读《鹧鸪天》,倍感绝望。这位姑娘到二十五六岁,才勉强找个婆家嫁了,后来见过几次,面容憔悴,腰身臃肿,心下甚为伤感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喜欢上一个女孩子,打击就特别沉重。
宋祁的另一首词,是得到词学家王国维激赏的《玉楼春》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是大家熟知的名句。那时,那份鲜活热闹,却不能安抚我受伤的心。
苏轼的词,也是我们都喜欢的。从少小到成人,奴化教育使我辈学会夹着尾巴做人,哪还有豪放的天性?我们却还是喜欢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:“大江东去,浪声沉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、三国孙吴赤壁。乱石崩云,惊涛掠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 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处、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是,笑我生华发。人生如寄,一尊还酹江月。”这是从《词林纪事》中录出,与他本多有不同。张宗橚说:“此从《容斋随笔》录出。容斋南渡人,去东坡不远,又本山谷手书,必非伪托。”我们不是研究者,凭了性情,去读诗读词,有所误读,也不在意,无非借诗词当酒,浇胸中块垒。也让委顿的精神,猛地一激灵 ,借苏轼豪放一把。
我在苏轼的一首《江城子》的天头,抄录了他的另一首《江城子》(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)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。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
尘满面,鬓如霜。 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。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”这当然是一首怀人的好词,但我当时何以会挑这首抄录在天头上,已无从回忆。我会怀什么人吗?那次短命的爱情,是很快被埋葬了。杜君则是不时可以见上一面的。我还会怀谁呢?
我自己也是“往事依稀浑是梦”了。
突然感觉身体不适,天光又尚早,便捧着《词林纪事》上床。很长时间没有就着床头灯读书了,都是在电脑前忙活。要是别的书,或许我早已扔掉书册,倒头睡去。我一页页翻过去,直到把它翻完。又回到第二六八页,对着天头的“往事依稀浑似梦,都随风雨到心头”出了会儿神。我已经知道这两句诗出自巴金的《家》。我固执地想弄清楚,何以杜君要把它写在这里?《词林纪事》自己能否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?
从第二六七页起,黄公度名字上有一个着重号,看来不是我所加。黄公度,字师宪,世居莆田,代多文人。但他自己直到四十八岁,才咸鱼翻身,一鸣惊人,搂了个状元在手。据说中状元之前,黄公度梦见雷电震闪,旗帜殷赫,果然以文章魁天下。杜君也曾做过什么梦吗?世评黄词“清而不激,和而不流”,还有人形容“宛转清丽,读者咀嚼于齿颊而不能已”。那时的我,却没有看出特别的好来。比如入选第一首《青玉案》:“邻鸡不管离怀苦,又还是催人去。回首高城音信阻,霜桥月馆,水村烟市,总是思君处。 裛残别袖燕支雨,谩留得愁千缕。欲倩归鸿分付与,鸿飞不住,倚栏无语,独立长天暮。”杜君却在《卜算子·别士季弟之官》上打了一个勾。这首词是:“薄宦各东西,往事随风雨。先自离歌不忍闻,又何况春将暮。 愁共落花多,人逐征鸿去。君向潇湘我向秦,后会知何处?”
我第一次拜会杜君时,我们聊开来,说到词上,就背诵起柳永的《八声甘州》“……不忍登高临远,望故乡渺邈,归思难收。……”一时心潮澎湃。杜君记起一首兄弟相别的诗:“还有讲两个弟兄,名字忘了,两弟兄当官后,聚在一起,相见后又要走……”我说:“执手相看泪眼,……”杜君立即否定:“不是那个!”杜君说:“哥哥写一首,弟弟还一首。……”找来老光镜,要把那首词找出来,翻了半天不见,只好自嘲地说:“以前一翻就翻到了,现在脑子不好使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”
杜君说的这首词,不就是黄公度的《卜算子》?
我往后面细寻下去,果然!
张宗橚引《知稼翁词注》说,士季是黄公度的从弟,名童,绍兴戊午同榜乙科及第,曾写过一首和词:“不忍更回头,别泪多于雨。肺腑相看四十秋,奚止朝朝暮暮。 何事值花时,又是匆匆去。过了阳关更向西,总是思兄处。”
兄弟之情,是说我和他吗?
我不敢问。
我记起早些年写过一篇《清明菜》,杜君读了,说这散文是写给他的。我偏愚钝,不知转弯,竟直说不完全是。见杜君有些讪讪,才后悔不跌,以至于今。杜君是早忘了这事的吧?我却每见杜君,都心下惴惴。
现在,我敢这样说,这篇文字,甚至这本小书,都是因杜君而写,为杜君而写的。
只是,“何事值花时,又是匆匆去”?两次拜访杜君,都在暮色四围,灯火已举时,又见面心切,都没来得及打量他的蛙园,观赏他的花草。《蛙园记》说“秋有黄花满径”,我们那时曾经多少次吟哦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啊!这个季节,怕早已是“满地黄花堆积”了吧?我本可以在龚滩再盘桓几日,我却不得不走。第二天我便要去酉阳,参加我的母校百年校庆。已经有一帮子朋友等在那里。等着举杯邀故旧,“痛说革命家史”。这便是事,是世事。真应了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。
但是,“过了阳关更向西,总是思兄处。”
这时,我才真正读懂了,杜君何以会喜欢黄公度,会在天头写上“往事依稀浑似梦,都随风雨到心头”,“肺腑相看四十秋”之后,还能够记起他们兄弟相聚又相别,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词作。
兄弟之情,朋友之谊,又不是杜君复杂精神世界的全部。
我在这册《词林纪事》的末尾,翻到一处深深的折痕,折叠起来,并不打开。我和杜君都嗜书如命,轻易不将书页折叠,有辱神圣。这是新的折痕吗?如果是,它要记下什么呢?
打开来,是朱熹惟一入选的词《水调歌头·隐括杜牧之九日齐州(他本作山)诗》:“江水浸云影,鸿雁欲南飞。携壶结客何处?空翠渺烟霏。尘世难逢一笑,况有紫萸黄菊,堪插满头归。风景今朝是,身世昔人非。 酬佳节,须酩酊,莫相违。人生如寄,何事辛苦怨斜晖。不尽今来古往,多少春花秋月,那更有危机。与问牛山客,何必泪沾衣。”
杜君曾说我是读了一遍《词林纪事》的,我却对朱熹的这首词没多大印象。我曾经做过唐诗的功课,倒是记得杜牧的原诗《七律·九日齐山登高》:“江涵秋影雁初飞,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将酩酊酬佳节,不用登临恨落晖。古往今来只如此,牛山何必独沾衣。”
在乡下种田的那些日子,我常用“但将酩酊酬佳节,不用登临恨落晖”来做自我安慰。其实每当佳节来临,想酪酊一回,也是一种奢侈。十岁时家里代供销社卖酒,看大人们喝得有滋有味,有次我自打了一两,一气喝下去,醉了整一个下午。之后在乡下再没醉过,因为酒再也不能随意喝到。杜诗一如佳酿美酒,每读必让人微醺一次,麻木一次。人生无常,古往今来,大家如此,你不必为个人的不幸而幽怨。
按方家的说法,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,叫隐括。此词,即隐括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一诗。朱子隐了多少括了多少,又有多少新的阐发,前人之述备矣,且不说它。我关心的是杜君读此词的感受。
杜君在“酬佳节,须酩酊,莫相违。人生如寄,何事辛苦怨斜晖。不尽今来古往,多少春花秋月,那更有危机”旁特别加了着重号。杜君年青时善饮,但不滥饮。每逢佳节,是会小饮一盅的。有朋自远方来,如果有酒存焉,也会排杯相待。借酒浇愁,我没见过,想来杜君深谙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(李白)。人生如寄,他将唐诗宋词做了美酒,愉悦自己,也麻醉自己。
有人解释说,无尽今来古往,多少春花秋月,概括绵延无尽的时间与上下无限的空间。往古来今谓之宙,四方上下谓之宇。作者精骛八极,思通千载,但觉无限宇宙之中,永远充满生机,哪有什么危机呢!作者是宋代著名儒家哲人。在儒家看来,宇宙、人生,本体为一,即生生不息的生机。这生机流行体现于天地万物人生,“亘古亘今,未尝有一息之间断。”(朱熹《中庸或问》)人生虽然有限,宇宙生机却是无限的。人生尽其意义,就是生得其所,体现了宇宙的本体,有限的人生便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。心知此意,则人生充满乐趣。
我不知道杜君是如何理解“危机”一词的。但我知道,我和杜君的周遭,都曾经危机四伏,甚至无力化解。杜君说自己其实是个胆小的人。但邪恶并不因你的胆小而不忍加害。杜君年轻时就曾被“情杀”而束手无策,坐以待毙,以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我们相交几十年,他甚至都没在我面前提起,他的人生命运,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对他的错爱而逆转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百般诱导,想为他释去精神重负,他还不想倒出来。
生性胆小,并不意味着逆来顺受。这种发乎内心的反抗,远比揭竿而起刺刀见红更为惨烈。
这是生命的心理玄机。
与杜君告别之后,踏着老街夜色回我下榻的地方。踯躇而行,脚步沉迟,真是思绪万千。
此时已经起更。老街一片微茫。几粒街灯,穿不透浓浓夜色,我连影子也没有投下。
说老街,其实我和杜君的抵足而眠,都不在现在的街面。那曾经的几个地方,都已被淹没水下。
在龚滩镇的下游,修建了一个大型电站,据称是第N个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。龚滩古镇不得不整体拆迁。地方政府当然无可奈何,修与不修,决策权不在他们手里。2007年,我作为被邀的作家采风团的一员,曾去参观过那座已然竣工的大坝。几座高大巍峨的山,被穿了个透心凉。同行的一位诗人,是我的好友,拒绝在大坝前照相留念。他掷地有声:“把大自然破坏成这个样子,还照什么相?”我深以为然。
库水淹没的不仅是过去的曾经的千年古镇,还有千年古镇的历史文化。
我曾站在拆迁之后重建的西秦会馆前徘徊。还有几块过去的石头。踱进门去,也还有一些过去的木柱和房梁。但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红庙子(西秦会馆的俗称)的味儿。大门上“西秦会馆”那几个字,从电脑里胡乱拣出,制做得十分拙劣。位置也不对,它应该在上街,怎么摆放在这里?我这样问街边的闲人。那人说,原来的位置摆放不下,只好放在这地场。这还怎么叫“修旧如旧”?
西秦会馆曾经是我很留恋的一个地方。从乡下来镇上,买一杯(竹筒所做量器)瓜子,陪那位曾经爱恋过的姑娘看电影,看什么电影不重要,重要的是看。那时这里做了区公所,来这里开个什么会,会散了,七八人围了一只大瓷盆,大块的炖肉,大碗的包谷酒,难得地享受一次,记忆犹新。50年代,西秦会馆旁边开有一家新华书店,一位漂亮的冉家女孩做店员,或许叫冉晓明?见得多了,我们就熟识起来。我自己掏钱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,就来自这家书店。每逢从30里外的山上来龚滩,即使当天要赶回去,我也会来书店看看。如果店门紧闭,我会怅然良久,怏怏而去。这家书店存在了很多年,直到老街之后修了条新街,它才搬走,和供销社挤在一起。
80年代供销社消失,书店也连同消失。新的商场建起来,旅馆修起来,餐饮业也十分兴旺,但再也没有一处卖书的地方。它不赚钱,没有人会关心它的有无。我不知道现在的电灯下,炉火旁,还会有多少人像当年我和杜君,捧了一本书,静静地读。
老街多年前有一位古董级的文化人罗子南,瘦而高,博闻强记,人称“龚滩通”。50年代为了个什么历史污点,曾被遣送新疆劳改。回龚滩后,又被遣送到一个高寒山上,守着鲁迅的几册单行本打熬时光。终于等到80年代改革开放,文化似乎被人们重新提起,子南老先生被当做文物发掘出来。可惜先生垂垂老矣,又无多余银两滋补身体,很快撒手人寰。
子南先生之外,杜君当堪重任。然杜君重病缠身,重振雄风,已觉力不从心。后生小辈们若何?
我和杜君就此有一段对话:
杜:“原来曾经风光一时,龚滩现在不行了,完全沉寂了。”
易:“文化那个是不必说。现在龚滩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文化。”
杜赞同地重复:“不可能有文化。”
易:“它诞生不出文化人。”
杜:“完全正确。”
易:“你说,文革前,文革中,都有像明昌兄这样的一代,可以说是……”
杜默然:……
罗子南和杜君的时代结束了。
我看到的是权力和金钱对人心的双重锈蚀。
在一套1936年版《词林纪事》不抵一两国酒茅台的时代,又复何言!
(我在网上曾查过,一套上下册的《词林纪事》,也无非几十元上下。)
龚滩是时代缩小了的一个盆景。
一个不再对文学阅读感兴趣的时代,是没有希望的时代。
作者简介:易光,男,重庆酉阳人,土家族。196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,做过木工,当过乡邮员。1977年参加高考,始得以离开乡村,进入城市。长期担任高校文学教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教授。1980年在《红岩》发表小说处女作。80年代主要从事小说、散文创作,有作品百余万字问世。代表作有小说《乌江故事》、《麒麟》等。90年代起主要从事文学批评。近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。有文学评论集《固守与叛离》(1997)、《阳光的垄断》(2002)、小说散文集《人迹》(2002)、学术专著《讲述与拯救:女性文学研究》(2011)及《重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》(2013)等出版。1999年起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《重庆文学史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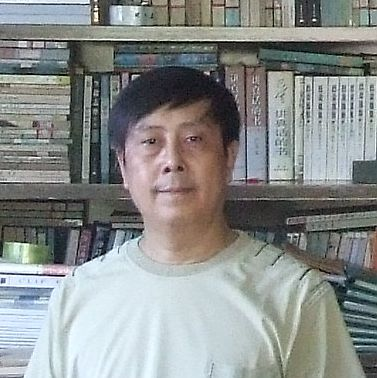
 贵公网安备52019002007322号
贵公网安备52019002007322号